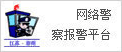为了科学,他们吃过8种蝌蚪、芥末味的蚜虫……
责任编辑:醉言 来源:中华网 时间:2018-06-29 06:12 热搜:科学 阅读量:10672
撰文 | Cara Giaimo
1972年,灵长类动物学家Richard Wrangham正在坦桑尼亚研究黑猩猩。尽管他已经每天都和黑猩猩生活在一起,听着它们的声音、闻着它们的气味,但他仍然希望能更深入地了解这些动物。于是,他向项目主管,著名灵长类动物学家简·古道尔(Jane Goodall)提出了一个请求:他想按黑猩猩的方式进食一会儿。
得到古道尔的准许后,Wrangham开始“享用”黑猩猩的食谱。这份食谱的主要内容是“味道糟糕至极,难以下咽的植物”。直到某一天,他尝试了一种黑猩猩吃剩下的美味:生的疣猴肉。
黑猩猩的疣猴食谱包括黑白疣猴、红疣猴这两类,但它们似乎尤其偏好后者,也更常捕捉红疣猴。Wrangham想要找出原因,因此他拾起黑猩猩吃剩的疣猴遗骸,每一类都来了一口。
“在我看来,它们的肉吃起来没有区别,”他写道。想到吃下的生疣猴肉和难吃的植物,他补充道,“这次经历告诉我,人类的饮食确有特别之处。”随后,他受此启发,写了一本书讲述烹饪在人类演化中起到的作用。
Richard Wrangham吃了一口红疣猴肉,这让他最终形成了人类演化的新理论。(图片来源:LAIKA AC)
我们往往将生物学看作一门可视化的学科:研究人员数着种群中的个体数目、观察它们的行为;他们剖析解剖学结构、追踪它们的生理反应。如果他们想进一步了解某样东西,就会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。
但正如Wrangham的研究案例,生物学还有着其他形式的知识。在一些情况下,品尝研究对象(或是研究对象的食物)能够帮助研究人员鉴别物种、解决逻辑上的困惑。同时,科学家能在这一过程中坚定自己的原则,或是从齿间发现更多谜团。有时,吃下一口苹果、蘑菇、蝌蚪或是蚜虫,就能帮助你解决困惑。
鉴别物种
Lactarius rubidus(一种乳菇)味如枫糖,这让它易于识别。(图片来源:NATHAN WILSON)
Peay说,在加利福尼亚州,有两种乳菇外形极为相似,并且这两种小个头的红色蘑菇都会在破损时释放乳白色的乳汁。“但其中一种乳菇干燥后闻起来、吃起来都如同枫糖,”Peay说,“人们将它添加到冰淇淋和饼干中。”而另一种乳菇有着胡椒味。“在野外,你可以捡起一株红色的乳菇,咬上一口,这样你就能鉴别它了。”Peay说。(编者注:虽然真菌学家给出了鉴别方式,但如果你不是行家,我们不建议你在野外试吃任何认识的不认识的蘑菇。)
对于很多植物,尝味鉴别法同样适用。“我经常会吃一些叶片,有时是为了鉴别,有时单纯是为了找乐子。”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城市生态学家Kevin Vega说。除了生物学,这种鉴别手段在一些出乎意料的领域也在使用。一些地貌学教科书建议“让泥土轻轻地在齿间摩擦”,以区分砂粒、粉砂粒与粘粒。古生物学家也有自己独特的鉴别技巧:骨骼化石碎片尝起来粘粘的,而岩石则不会。
解决疑惑
像Wrangham这类生物学家常常面临着复杂的难题,而解决途径有时正是自己的舌头。1971年,为了探究游得慢的蝌蚪是否会演化出糟糕的口味以抵御捕食者,动物学家Richard Wassersug说服他的研究生吃下8个不同物种的蝌蚪。“每一种都不甜美、不好吃。”Wassersug说,不过他们发现,游得最慢的蝌蚪口感最为粗糙。
在Wassersug的测试中,树蛙的蝌蚪属于中等口感。(图片来源:GEOFF GALLICE)
与此相似,爬虫学家Chris Austin多年来一直希望解释,为什么一些石龙子的血液是绿色,而另一些是红色的。他曾分别生吃过这两类石龙子,以期找出两者口感上的差别。不幸的是,两者都很难吃:“就像放坏了的寿司。”他描述道。现在,Austin还在探究这个问题,不过至少,味觉试验帮助他获得了额外的数据点。
保护生物学家Karl Magnacca读博期间曾经调查一种夏威夷的叶舌蜂,这是美国最为濒危的蜜蜂之一。多数蜜蜂用腿上的毛携带花粉,但这些叶舌蜂却是先将花粉吞下,返回蜂巢后,再将花粉吐出。“如果你抓到一只正飞回蜂巢的雌性叶舌蜂,它很可能会将花粉呕到你手上,以此作为一种防御机制。”Magnacca说。
这时,你可以将呕吐物放在显微镜下,研究它们喜欢光顾哪些花朵。或者,不用等到显微镜登场,你可以直接吃下蜜蜂的呕吐物,通过味道判断花粉种类。至少,Magnacca已经试过好几次了。不幸的是,多数蜜蜂的呕吐物尝起来都差不多,还是显微镜提供的信息更全面。“这些蜜蜂几乎只光顾当地的植物,”Magnacca从中了解到,“这似乎是限制其生活区域的重要因素。”
夏威夷考艾岛上的叶舌蜂。(图片来源:FOREST AND KIM STARR)
有时,味觉本身也能激起求知欲。当Stephanie Guertin在罗德岛大学读神经科学的PhD时,她在实验室研究龙虾的攻击行为。试验中,龙虾两两一组被放入水箱中,其中一只暴露在一类化学物质中,这类物质会让它误以为,同伴的体型比实际要大很多,并因此处于恐慌中。由于政策禁止研究人员将实验对象放归野外,实验室成员选择将它们装进肚里。
“就这样,吃了很多只龙虾后,我注意到它们的口味有些区别,”Guertin说,“我开始注意观察,这些龙虾是不是在水箱中受到惊吓的。有趣的是,受到惊吓的龙虾尝起来有点酸。”她邀请一些朋友进行盲测,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。尽管她没有更加严格地验证这一点,对猪、牛、羊、火鸡等其他动物的研究已经证实了,压力下释放的化学物质会影响动物的口感。
合乎逻辑
在一些情况下,吃掉(或是吸入)研究样本完全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决定。一位蚜虫研究者写道,吃下实验对象让他们更容易准确数出实验对象的数量。(多说一句,如果这些蚜虫已经咀嚼了十字花科植物的叶片,它们吃起来是芥末味的。)
从贝加尔湖中打捞出的贝加尔湖油鱼。(图片来源:BR?CKE-OSTEUROPA)
Leslie Ordal讲述了她在西伯利亚进行野外考察时发生的故事。当时,她与同事在贝加尔湖研究贝加尔湖油鱼——一种凝胶状的底栖鱼。人们不会吃这种鱼,在西方科学文献中,有很多关于它的未解之谜:“它曾被描述成一种透明的、在阳光下快速溶解的鱼。”Ordal写道。研究团队没法把福尔马林从美国带到西伯利亚,为了保存标本,他们在俄罗斯买了当地特产——伏特加酒作为替代。同时,他们还买了一些品质更好的伏特加自己喝。
一天夜里,他们发现好的伏特加酒已经喝完了。“我的一些同事并不想因为这种事扫了兴致,他们溜进野外实验室,径直走向了装死鱼的瓶子,”她写道,“这些人从一瓶酒里啜了几小口,这时,他们喝醉的逻辑意识到,其中一瓶伏特加少了一些,这样太过明显。于是,他们每瓶酒都又喝了一点,让它们重新回到同一高度。”
这件糗事带来了意料之外的成果:人们此前认为这些鱼十分脆弱,但它们的标本从摇晃过程中完好保存了下来,这否定了先前的认识。
教育意义
这些故事可能让你看得目瞪口呆,但事实上,这里并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。生物学家花费大量时间研究他们的实验对象,一定程度上,我们能够理解,其中一些人想要吃掉它们,或是像它们一样进食。“并非所有无脊椎动物实验室都有这个传统,但很多实验室都会这样,在可行的情况下吃掉实验对象。”新墨西哥理工大学的无脊椎学家Lindsay Waldrop说。就在最近,Waldrop还为她的本科生制作了油炸海鞘。
盘子里的就是Waldrop制作的油炸海鞘。(图片来源:DR。 LINDSAY WALDROP)
尽管海鞘在智利、韩国等地被视作美味佳肴,Waldrop和她的学生通常只能在解剖台上接触到海鞘。“它们很难吃,像皮革一样难以下咽。”Waldrop这样评价。她在自己的学术生涯里已经品尝过各种美味:在华盛顿圣胡安岛的野外工作站工作时,她和同事从虾到蠕虫再到海胆吃了个遍。“我们吃了许多种东西,只要不会刺痛你、让你不舒服就都会吃,”她回忆道,“我猜想,我们没有百分百遵守安全协议,但这是很好的传统。”
在环境行为研究公民实验室(CLEAR),食用标本是科学研究的重要一环。CLEAR的大量研究都在关注塑料污染对纽芬兰及周边食物物种的影响,他们的很多样本都是从当地猎人及渔民手中买下的。“如果进行对食物的研究,但我们只捕获动物却不吃它们,这显得有一点倒退,”CLEAR的主管Max Liboiron说,“这样一来,你研究的就只是物种,而不是食物。”
在纽芬兰的CLEAR,研究与食用是紧密相连的。(图片来源:MAX LIBOIRON)
为了让食用样本合乎规章制度,实验室对一些条款进行了修改。“在多数大学的动物关怀协议中,动物组织都被称作危险废物,”Liboiron说,“我们制定动物尊重准则的第一步,就是改变这种情况。”现在,在鳕鱼、鸭、鹅等动物身上做完试验后,他们会尽可能把能吃的部分都吃了。如果是不能吃的,他们会将遗骸放回它们原来的环境中,让它们回归食物网。在Liboiron看来,吃下实验动物意味着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好。
这些为了科学而吃下的动物并不都是那么美味,但在文中所分享的案例中,对这种特殊关系的理解,能让这种体验变得更有价值。在某些情况下,甚至值得重复尝试。Wrangham还没有重复他吃生疣猴肉的试验,但如果有机会,他可能会重新一试:“我怀疑可能不是因为黑白疣猴肉味道不好,而是它们的皮不好吃,”Wrangham说,“我必须再试一次。”
郑重声明:此文内容为本网站转载企业宣传资讯,目的在于传播更多信息,与本站立场无关。仅供读者参考,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。
相关文章